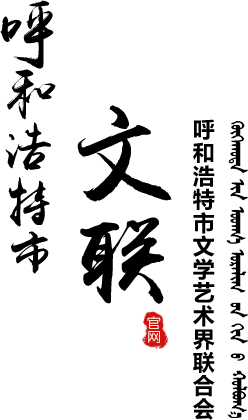书商乎?书疡乎? ——徐扬长篇小说《书商》的文化与社会思索
来源: 作者:蓝冰 发布日期:2024-03-06 16:09:51
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膨胀的时代,消费主导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仿佛是海上的一艘船,当风浪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危险却没有力量对抗危险。对于消费的盲目崇拜和需求,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一切都变成生产,一切变成消费。当精神产品的能指和所指互换并混乱,也就是说当书籍这一具有一定的商品性的特殊商品蜕变成完全的商品,著述和阅读变成真正的生产和消费的时候,人类精神家园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人类脆弱的情感、价值观、社会秩序都面临着灾难性的打击。徐扬先生的长篇小说《书商》(又名《书殇》)正是从这一庄严的思考显示其不同一般同类书籍的价值。
书商这一职业,古已有之。对文化的发展起到过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首先对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就功不可没,有些书商甚至对于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南宋的陈起就在江湖诗派的形成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现在我们还能见到的各种童蒙读物,经典古籍,古书善本,其作用就更不言而喻了。他们也有商品性,但其文化功能即其所指还是主要的。当然也有劣迹,为了利益,迎合低级趣味,诲淫诲盗也是时而有之的,然而识文断字的人在过去毕竟只是少数,影响终究不是很大。
产生巨大的冲击。徐扬先生正是紧紧扣住了时代的脉搏,极其睿智地抓住了“书商”这个联系知识与经济的特殊群体,通过胡宝山等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塑造,细致刻画了这一群体。他们或艰难挣扎、或投机钻营,或狡诈奸佞……等等不一而足。而真正的书籍著述者却在这样的社会状态前茫然不知所措。于是早期的书籍市场(通常称二渠道)制造与流通是在一群文盲无赖的侍弄下,昔日的“桃花源”现在到处弥漫着铜臭的气息,其间人性与兽性、爱情与欲望、权力与金钱无所不备,也是人生之一具体而微的全景鸟瞰。
然而小说的意旨远不止于此,似乎又有着更深的思索和无奈。小说以三位人生轨迹迥异的女性为粘合剂,描写了以她为中心的一批书商和所谓文化人,通过二位丽人搅起的风风雨雨展现了以寒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清醒与麻木,原则和规则之间的矛盾。书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久站鞋湿,或主动或被动地拒斥着、接近着、接受着消费社会,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们的矛盾在于既想坚持固有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又想摆脱经济困境,既想坚持文化事业的神圣性,又不知不觉举起了向“金钱和世俗”投降的白旗。在这个形势下,两全其美是一个梦想。明哲保身也没有可能。在整体的挣扎中,很多人经历着见利忘义的蜕变,昔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也日益粗鄙,庸俗,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纵容人性情感中低俗和脆弱的方面,文学在这样的洪流中变得时尚,肤浅,世故,矫情,丧失了本该具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功能,即使偶有批判也不过是扭捏作态的表演罢了。
小说以此真正实现了对书生灵魂的拷问,生动再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心灵蜕变,表达了作者对于文化,文人往何处去的优虑,深刻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
“世界上要是没有了女人,男人就都变成野兽了”,三位女性是联系文本中人物的纽带,小说全篇也正是以三个女人为中心的三条线索相互交织而成。她们分别是艾婷婷,安谧,水淼淼。艾是一个文弱的知识青年,具有外柔内刚的性格,为了走出不幸的婚姻,也为了爱情投身商海。安是一个导演,像很多女人一样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一个已婚男人的身上,出发点已错,又所托非人,结局很惨。水则是一个大胆泼辣的投机主义者,金钱至上的忠实信徒,为了利益可以赌上爱情和灵魂。小说由艾写起,家庭不幸的她在惨遭毒打之后投奔她惟一的朋友安,此时的安已做了宣传部长萧雨浓的情人,因萧的缘故,艾认识了身为文学小刊落魄编辑的寒冰,寒冰是萧的大学同学,空有一腔文学理想却被现实撞得粉碎,酒席间艾与寒相见恨晚,后来由于艾的支持,寒冰坚定了要自己打拼一片天下的决心。他也做起了书商,因为商业的关系认识了流氓书商胡宝山,而我们的第三位主人公水就是他的“情人”,关系看似复杂实则脉络非常清晰,这其中涉及文坛,官场,商场。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场关于欲望、金钱、权力,自由全面的斗争。
寒冰的刊物面临破产求助于身在官场的同学萧,萧的袖手旁观与胡宝山的教唆使得这个对商品经济大潮还采取观望态度的文学青年,逐渐挽起了裤腿,艾的追随更使他如虎添翼,然而毕竟修行尚浅,吃点苦头交些学费也是难免的,在这磕磕绊绊中他们开始发现文化人儒雅君子的一套全无用处,与胡和水的简单直接相比甚至有些酸腐,坏人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不遵守任何你不喜欢的规则,好人则处处受限,胡可以大声叫嚣:“钱,钱就是一切。”水也可以直白就想作杨玉环,就想当祸水,还附庸风雅地背几首唐诗装点门面。从某种角度来说艾对水的欣赏实际上是对自己过去的一种否定。几经打拼,虽然也有徘徊和挣扎,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寒冰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进商海,从一个书生向一个商人蜕变,适者生存的法则是残酷的,寒冰不得不抛弃“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轻易地失守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胡宝山是书商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当然也是作者不吝笔墨刻画的人物之一,这是一个半文盲的书商,粗鄙狡诈却深谙经商之道。满嘴脏话,嗜赌成性,酒席上屡发高论,虽字字铜臭却又无懈可击。胡宝山与水淼淼也只是相互利用,只要时机成熟,一定会倒戈相向,果然在利益问题上反目成仇后落了个同归于尽的下场。
安谧把感情的赌注全都压在小官僚萧雨农的身上,以为找到了归宿。可这个表里不一的家伙只把她当做灵魂的避难所,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他可以出卖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灵魂。安只是他的工具——抚慰自己,压制宿敌的工具。安谧和吕海涛苦心经营的专题片最后竟被左删右减成为了他升官发财的筹码,在他最终如愿以偿地登上副书记的宝座以后,他抛弃了安谧,成为安谧投海自尽的直接凶手,以萧为突破口,作者对于官场黑暗的揭露也是不遗余力。在杂志《花苑》的审查问题上,胡宝山念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说有问题就有问题没有也有;下联是,说没问题就没问题有也没有;横联是,绝对权威。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安谧调到文联后讨要经费时遭到李科长侮辱,堂堂党的干部竟说:“你陪爷睡一次,就把款拨给你。”淫逸无耻之态一览无余。
抛开这些细节不谈,综观全篇,小说写作的意义正在于它有力地揭示了文化人内心在这一剧变时期的痛苦,焦虑和精神的裂变。
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两栖的,“学而优则仕”是孔老夫子留下的古训。他们在很多时候都是一只脚踩在学术文化上,另一脚踩在政治仕途上。政治意识形态遭到解构以后,那另一只脚就自然落在了经济利益上。文化与政治的联合或许还可以兴邦安国,而与经济的联合却最容易引发堕落,引发妥协。文学是不能掺杂太多功利色彩的,掺杂的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各种低级、矫情的言情、武侠作品蜂拥而至,色情,暴力一应俱全,残雪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世俗生活犹如滚滚的车轮碾过一切,一个人如果要在世俗强权威胁时仍然保持她内心领地的完整,她就只有不停地分裂自身,不停地进行高难度的灵魂操练,以使自身在那片无疆国土上进行不懈探索的工作”。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文化人要么害怕被击倒而躲避敌人,要么没战斗就乖乖举起了白旗。这样说来,文化的堕落就是文人的堕落,文化的庸俗就是文人的庸俗,知识分子的这种骑墙做派由来已久,他们有太多的依附性,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批判意识和机制。拯救天下的崇高意识下裹藏着无意识的功利主义,迪特利奇就称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向体制投降的一群人,正是这样使得攻陷他们的精神家园轻而易举。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更多观望的人挽起裤腿走下水去。
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家对于文化产业走向的深深忧虑,出版什么样的书?以什么形式出版?都以经济效益为准绳,《姓学探源》只需改作《性学探源》就能热卖;将作者写为仝镛、全镛作品就能畅销,这是多么荒诞的逻辑。文化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大众文化是市场与文化妥协的产物。这种文化的内质是市场效益,而进入市场就必须遵循市场运行的规则。为取媚于观众,就必然导致对文化深度的降格以求,文学变得不再追求对艺术,社会,人生,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探索,文学家也放弃了他们应有的良知和真诚,而是着力创造直接的感官刺激,在轻松娱乐上做文章,搞一些泛滥的煽情,艺术的惟一性,独创性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情节相似的故事,千人一面的人物,而读者又都乐此不疲,安于受骗,就这样在全民浮躁的参与下,精英文化被放逐了,被同化了,丧失了其监督、否定的功能。然而精英文化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良心,是历史传承的纽带,是我们可以诗意栖居的家园。面对这来势汹涌的滑坡与沦丧,有良知的文化人不该保持一份应有的清醒与自觉吗?
读罢徐扬先生的《书殇》,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不禁要问,这部发人深省的著作究竟是在说书商,还是在为书殇?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能思索这样的问题并能热衷这样的问题,说明知识分子还有救,社会上还有他们的意义、位置和价值。小说笔调优美,对人性和社会的思索深刻而独到,尤其是对各阶层人的心理的揭示尤见功力。这是该小说欣赏的起点,值得关注。
据《呼和浩特文艺》2017年第2期